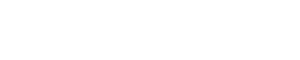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93节
作品:《新顺1730精校版》了拼命的时候了,斜坡的最后一段,得靠他们这些有勋位的老兵和军官冲开了。
这是最后一搏了。谁都清楚,再无法突破,军心就崩了。
“只解沙场为国死,何须马革裹尸还?!”
几十人齐声呼喝,喝完碗中的酒,一起摔了断头的酒碗,扔了头盔、卸了挡不住铅弹的甲,只在额头上绑上了武士赤帻。
声声碎,出了帐篷,有人把身上所有的银子都摸了出来,朝着那些默默站立送他们最后一程的士兵扔去。
银钱如雨,纷纷落下,却无人去拾。
“弟兄们,打完仗买碗酒喝,当我请的!”
“老子用不到这东西了!”
说罢,这几十名最精锐的老兵、军官,走向了战场,去突破那一段已经让躺下了六百余具尸体的斜坡。
再无法突破,军心真的就崩了。
第065章 报捷
嫩江下游,皇帝行营。
李淦如同痔疮犯了一般,背着手在大帐内来回踱步,根本停不下来。
时不时叫太监拉开大帐,探头出去看看,希望能够看到手持蓝旗报捷的骑士。
前线这几天传来的消息很不乐观。
都知道刘钰年纪小,又没上过战场,对于当初刘钰的奏折,不少老将看过之后虽觉有理,但恐怕不过是个赵括,又或许危言耸听以彰其懂西学之名。
可现在前线的情况真的如刘钰预料的一样,前锋部对木里吉卫连续九天的攻击,损兵折将,至今未下。
尤其是前线每日三封的奏报,更是验证了刘钰的话:强攻棱堡,死伤最惨重的地方就是最靠近棱堡的那段斜坡,攻取要有技巧。
当初这句话刘钰出于不可告人的“变革需要几千人命做代价”的目的,根本没有着重阐述,隐藏在一堆废话中,一笔带过。
而现在,当初一笔带过的话,被翻出来,就成了预言。
九天激战,六百将士阵亡,受伤者不计其数。如果不是抽调的全国精锐、如果不是皇帝亲临前线不远,仗打到这个份上,军心已经崩溃,没办法再攻了。
守卫堡垒的罗刹人很狡猾。
攻城的第一天,守城的罗刹炮兵稀稀疏疏地开了两炮。
装了半份火药,调整了炮口仰角,使得前线的攻城主将误判了罗刹火炮的射程。
误判的火炮射程,导致攻城出击的集结点选的过于靠前,集结过程中遭受了罗刹火炮的突袭,损失惨重。
靖国公袁岚的孙子当场被罗刹的炮弹砸断了腿,流血过多,不治身亡。
随后的炮战中,大顺的重炮还没来得及完全摧毁罗刹的火炮,皇帝军令如山必须十五日破城的压迫下,就发动了强攻。
在两道护城壕前的斜坡处,遭受了罗刹的交叉火力袭击,尸体把一段壕沟都填平了。
李淦终究是第一次出征,皇帝御驾亲征,在盛世之时,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好不要去。
现在,距离约定好的与喀尔喀蒙古诸部首领会面的日子越发接近,前线仍旧没有传来好消息,李淦真真是心急如焚。
增兵无用,根本无法展开,只能催促吉林防御使继续转运下游的火炮。
可又恰逢一场山雨,松花江水猛涨,沿途泥泞,加强前线的火炮也不顺利。
大帐内,几名军中实权派的老勋贵坐在军凳下,浑身着甲,一言不发。
靖国公袁岚已然六十八岁,常年驻守热河一线,压制漠南蒙古,先祖袁宗第;鄂国公李九思,祖上是人称小尉迟、万人敌的李定国,张献忠死后复旧姓,在刘体纯的斡旋下归顺抗清,也封了个如尉迟敬德一样的爵号,如今掌管京营操练;淄川侯谢无忌,祖上被满清称之为山东第一巨寇,曾活剐过孙之獬,如今出镇辽东,之前负责修建驿站。
刚刚经历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的景国公袁岚,手里捧着一本《旧唐书》,故意装作一副镇定的样子。
可那一篇《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列传》已经半个多时辰还没翻过去,手指摁住的位置正是惨烈的“石堡城之战”。
他很清楚,皇帝是第一次出征,这个时候,自己这些老勋贵就是皇帝的主心骨。若是也和皇帝一样焦躁不安,皇帝只怕会更加不安。
哪怕自己的嫡孙刚死,他也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焦虑,只能用沉默来让皇帝安定下来。
许久,袁岚终于放下了那本《旧唐书》,起身道:“陛下请安坐。幸太宗之远见,武德宫必考几何测量之法,我军炮术不弱罗刹太多。罗刹虽拒堡而守,亦不可持久。”
“为人君者,当计天下,而非一城一堡之得失。况且这几日天气晴好,无有雨云。前线儿郎既已决死,此堡必下。”
李淦看了看这位刚经历过丧孙之痛的老臣,叹了口气。
见大帐内气氛沉闷,终于道:“卿等不需如此。罗刹人不过数千,非是当年萧太后之辽带甲数十万;朕也不是敢去封禅却不敢去前线的真宗,你们不必学寇莱公,做镇定之状以安朕心。”
“朕所忧者,非在此堡,而在之后。此堡纵然攻下,罗刹尚有数堡,又将如何?重炮转运不易,兵贵神速,务必要在冬日初雪之前攻入捕鱼儿海,否则罗刹一旦增兵,联络准噶尔部,又将如何?”
同样垂暮的鄂国公李九思起身道:“陛下所忧甚是。然如太宗所言,凡事当以辩证。陛下此番亲征,所谋者,喀尔喀蒙古。”
“喀尔喀蒙古,所忧者,准噶尔。臣于天朝、罗刹,依旧可为一方之主。可若被准噶尔击破,则必被收其众、夺草场。”
“以辩证之言,若罗刹联络准噶尔,则喀尔喀部非忠天朝不可,亦非全是坏事。”
“刘守常言:罗刹苦寒,又多征蒙古诸部从军,且信东正而非红黄教。喀尔喀部若非不得已,当不会投罗刹。”
“他虽年幼,依臣之间,守常非幼常,非夸夸其谈之辈,大有道理。”
这是老成之言,李淦心里也明白,可还是叹息道:“唐时,太宗时候,诸夷臣服,未有敢叛者;及至安史后,夷狄反叛、此起彼伏。前后迥异,何也?天朝甲兵自强,则夷狄服;甲兵孱弱,则夷狄叛。”
“如今朕欲定北疆之患,岂能全部指望罗刹与准噶尔给喀尔喀部的威胁?”
“此番必要展我天朝军威,威慑其众。《通鉴》言:畏威而不怀德,此言诚不我欺。”
“此番北上,一则定罗刹边疆;二则示威于喀尔喀部,若只成其一,未竟全功,日后北疆何宁?”
“就算喀尔喀部因为准噶尔的威胁归顺,西京乃我朝龙兴之地,岂容他人酣睡?准噶尔部必要除掉,除掉之后,喀尔喀部没了准噶尔部的威胁,难道就不会再转而投罗刹?”
“是故此战,一定要打的叫喀尔喀人震撼心服,数十年内不敢有异心。他们打不过准噶尔,准噶尔打不过罗刹,我军若是能大败罗刹,喀尔喀人自然清楚,该忠顺于谁,也才能延续当年太宗遗训,分封建制,众分其力,一如漠南模样,绝我天朝千五百年之北患!”
“现如今,木里吉卫城之战,精锐云集,重炮齐备,结果打成这个样子!喀尔喀部若来,会怎么想?罗刹人不过数百,甚至都非是罗刹精锐京营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