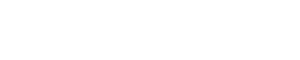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29节
作品:《新顺1730精校版》推陈出新,新编练一套战法,足以攻城略地战无不胜。
这等同于偷换了一下概念,把“中学为体”的中学,直接换成了古人的智慧,而非是经史子集。
但正所谓“六经注我、我注六经”。
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,到底如何解释,自然还轮不到一个小小的刘钰,还要看皇帝希望怎么解释,怎么定义为体的“中学”到底是哪些。
又如刘钰刚才说的,蒙元时候工匠封万户侯的事,这算是啥?
是体?还是用?
是用的话,那就动摇了体——樊迟问种地的事,孔子说什么叫小人?这就叫小人啊,只要学好礼仪,四方的百姓就会来投奔,哪里用得着学种地呢——如果工匠也能封万户,那天朝与夷狄又有什么区别?
所以,这个西学为用的“用”,用到什么程度?哪些可以用?
以用逼体,这是无解的:轻视工匠,火器与科技肯定不如西方;重视工匠,那就是天朝体系的崩塌,士大夫定然不屑与工匠同堂。
工匠要是和士大夫们一起站在朝堂,但凡有点血性的士大夫,就会回去投湖自尽的。
李淦没有说话,而是细细琢磨了一番刘钰的话,久久不语。
其余和刘钰一起跪着的人,却是暗暗心惊刘钰的胆子真的有够大,本来这件事马上就要了了,这时候却偏偏又说这些话,这不是没事找事吗?
几人心想,入恁娘的,以后你刘守常叫我们去干啥,都得先琢磨琢磨。再不敢听你的了,这是要吓死人啊。
胆子这么大,迟早要吃亏的。见好就收吧,兄弟。
李淦倒是很欣赏刘钰的胆大,之前他就开过玩笑,说缩头缩脑的老王八生出来个横行无忌的螃蟹。
只是刘钰说的这番话,李淦越是爱才,就越得不置可否。
福建教案引发的导火索,导致朝中大乱,党争将起。
西法党、守旧党争执不堪,耶稣会那边又火上添油地传来了教廷谕令,这样的风口浪尖上,两边都只能走极端。
守旧党必须要极为守旧复古,才可被守旧党看成自己人;西法党又要极端激进,才能被西法党看成自己人。
谁站在中间,尤其是什么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之类的话,那是要被两边攻讦的。
即便刘钰身后还有个翼国公,但这样的风口浪尖,哪里是一个武德宫的十七八岁少年能顶得住的?
只有到两边斗的两败俱伤时候,皇帝才能居中调和。那时候双方都斗的没了力气,也能接受这个折中之策。
尤其是刘钰身上还有个大污点、大麻烦——之前和传教士走的太近,如今又弄出个热气球飞升,御史言官一句“窥探禁宫、大不敬”,便是翼国公都扛不住。
想到这,出于保护,李淦笑道:“孩子话。你懂什么是体?什么是用?你做的这大孔明灯,无非是术,不足称道。”
刘钰也是铁了心了,得寸进尺,见皇帝没有苛责的意思,又道:“陛下,术变了多了,道还能是原来的道吗?我听那些传教士说,西夷已用自生火铳,却不知陛下是否知晓?”
自生火铳,也就是所谓的燧发枪。
李淦点头道:“朕知道,无非是自生火铳,晾也没什么特殊。只是施放便利一些,那些传教士也曾贡给朕几支,时常还有燧石不发火的情况。倒也不见得就多好。”
燧发枪的点火率确实是个问题,即便再发展几十年,燧石激发的火星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点燃引药。在发火率上,肯定是不如明火的火绳枪的。
但新事物总是有进步空间的,尤其是单看燧发枪算不得什么,可配上一整套与之相配套的军事体制改革,那就远远超越了大顺的火绳枪、冷兵器混编;靠数量优势的大炮来殴打周边小朋友的战术体制了。
刘钰见皇帝这么说,眼珠一转,想到了一番话。不但可以继续试探,至少在皇帝心里留下一些变革的种子,也顺便清洗一下自己和传教士来往过密的传闻。
这时候,是该卖队友、卖师傅了。
“陛下,我家中也有传教士带来的自生火铳。只是,那些西洋传教士说的并不完全,不敢说包藏祸心,但恐怕他们也是一知半解。”
“只论自生火铳,比之火绳鸟枪,或许进步不大。但其实我多方打听才知道,西洋除了用燧发枪外,更有刺刀一物,那才是关键之物。如此一来,就可谓是术大变,则旧道不通,导致整个战法都变了。”
“那些传教士亦或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亦或许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,却只说其一不说其二,我才忧虑万分。”
第021章 纸上谈兵
什么叫莫须有?
这就叫莫须有。
传教士懂个屁的军事体系?
术业有专攻,加上此时获取知识的成本太高,刘钰确信这些传教士根本不可能懂军事变革的脉络。
尤其是这些传教士不会明白,引发这一轮军事变革的,不是看起来精巧的燧发枪枪机,而是不显眼似乎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刺刀。
他明白,所以才要莫须有——诛心之言,传教士可能是很清楚,但是故意不告诉咱们,这帮人不是什么好鸟。
轻飘飘的几句话,既勾起了皇帝的兴趣,也撇清了自己和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事实。
顺带着,把一定无比巨大的大黑锅,扣在了自己曾经“得师事之”的戴进贤等传教士的头上。
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还是明知而故意只说其一不说其二,那就看皇帝怎么想了。
刘钰从父亲和齐国公那已然了解朝廷将来可能禁教的态度,很明确。
这时候自然要撇清、洗白。
传教士这艘破船要沉,自己可没心思去陪着一起沉。
卖了旧人,再扣一个大黑锅,踢上一脚。
那他刘钰就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,最起码也是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国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”。
忠心耿耿,大为可用啊。
传教士的一知半解,配上文人的那张嘴,照着正常发展的趋势,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
就前朝文人见到荷兰武装商船记载“船巨阔数十丈、一炮糜烂十余里”的德行,指望他们去考察军事体制,那是做梦。
李淦被刘钰的话弄得一怔。
这话若是别人说,李淦未必能信,甚至觉得这是故意生事、无中生有,莫须有之罪。
可他刚刚看过刘钰写的《西洋诸国略考》,里面的一些东西,便是那些传教士也说不了那么透彻。
这问题就来了。
没有生而知之者。
刘钰知道,那得有人告诉他。
就算是他旁敲侧击问的,那也得有人知道。
朝中传教士颇多,为什么没有人说的那么清楚?
尤其是在翻译的称呼上,为什么遮遮掩掩那个万王之王的称号?
总不成这刘钰是生而知之者,在家坐着就知道万里之外的事吧?
很显然,是传教士自己不说,这个刘钰有心算无心,旁敲侧击之下,才知道的嘛。
传教士知道却不说,这不是其心可诛是什么?
这似乎很合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