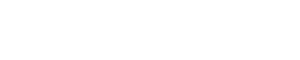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131节
作品:《三国模拟器:这个马谡太稳健了精校版》家住在哪了。”
“……”
诸葛亮最终还是派人把马谡送回了府上,一并送过来的,还有包裹的严严实实,依旧难掩窈窕身姿的羌女。
于是,在一个大冬天的黄昏,一男一女伫立在成都街头,一座参将府的门口,迟疑不前。
参将府大门口,四个士兵正望着两个人窃窃私语。
第一个士兵说:“我来了三个月,还没见过马将军,要说这差事可真轻松呀,主家只有一个夫人和五个男孩,主夫整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府上又和和美美,不生争风吃醋那种事端。这日子可真让人羡慕,倘若我是马将军,我做梦都会笑醒。”
第二个士兵说:“谁说不是呢,我来了六个月,也没见过马将军。倘若我是马将军,无论成都花街柳巷里的姑娘们再妖娆,我都绝不会动摇半分。”
第三个士兵说:“唉,我与你们一样,来了九个月,也没见过马将军,不过,我听说马将军在外面找了一个相好的,长得可带劲啦,那姑娘胸脯有这么大,腿有这么长,腰肢却只有这么细。”
言语间,他先比划了出两个馒头的形状,紧接着比划出到自己胸口的长度,最后则是两拃对在一处,比划了个约莫正常人脖颈粗细的单位。
众人立即倒吸一口凉气,对第三个士兵所描述的场景向往不已,连忙偷偷呲溜了一口口水。
如果是这样的女子的话……那也不是不可以出轨一下。
第四个士兵一脸羡慕道:“也不知道马将军到底是何等的英姿勃发,居然有这般艳福。你们有所不知,我来了一年,也不曾见过马将军呐。”
马谡施施然走到四人面前:“我就是马将军。”
“听说你们要见我?”
第117章 马氏五子,老二最苦
还未更名为雍州刺史府的参将府中,内堂。
啪啪啪,啪啪啪……
肌肤遭受拍击的声音络绎不绝,密集且激烈,
让人听了头皮发麻。
三岁半的马谦流着大鼻涕,仰着头,眼神里透露着无边的害怕。
他从不曾见过向来温润和蔼的阿母发这么大的火,也不曾见到十五岁的大哥马温挨过这么狠的打。
就因为大哥顶了阿母一嘴。
马谦的小脑袋瓜有点想不明白,为什么同样是顶撞阿母,三岁半的他就不会挨打,还会被阿母抱在怀里一顿亲热,并夸赞一句“我儿乖啊”,而大哥顶撞了阿母,就会被竹板打手心。
难道是大哥有点大了?
他同样想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、很多。
譬如说:人为什么要戒奶?为什么不能一直吃下去呢?奶奶那么香甜可口!
譬如说:十二岁的二哥为什么叫马俭而不是叫马良?
启蒙先生前段时间才告诉过他,兄弟五人的名字是按照“温良恭顺谦”的顺序起的,所以二哥为什么不叫马良呢?
他想不明白,三哥马恭为什么九岁了还尿床,他三岁都不尿床了,就算阿母夜里不定时给他把……他也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尿床。
他都不是三岁小孩了。
还有,六岁的四哥明明叫马顺,却为什么倔犟的像头驴?天天被母亲打,还不改。
马谦最想不明白的是,他好像有父亲,又好像没有。
每次哥哥们自豪的说起与父亲(马谡)之间的趣事时,他都只能眼巴巴的羡慕到瞪大眼睛。
他还没见过父亲……或许见过,但他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了。
马谦一直都很会看眼色,通常阿母发脾气的时候,他都格外乖顺,随叫随到、指哪打哪。所以,刚才阿母叫他把竹板拿来时,他就屁颠屁颠跑去把竹板给拿来了,而不是劝阿母不要打大哥。
所以,这会他被大哥那恶狠狠的眼神盯的有些害怕。
于是,他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,坐在地上蹬着小短腿,不依不饶告状道:“娘亲,大哥他瞪我,我好害怕……好害怕……”
啪啪啪的声音顿时响得更急促了。
马谦又哭了一小会,这才满意地收起了撒泼。
及看到大哥眼里闪过求饶、憋屈、还有无奈的神色。他从地上爬起来,抱住母亲的一只膝盖,给大哥做了个鬼脸。
哼,竟敢惹我,这个家里谁地位最高,大哥心里没数吗?
没数吗?!
做完鬼脸,马谦忽然瞪大了眼睛,望着堂屋门口,僵住。
忘记了说话。
门口站着一个男人,很高很大。
马谦觉得这个男人有些眼熟,但是小脑袋瓜有点想不起来了。
马夫人很快感受到了稚子的反常,停下教训长子的行为,先低头瞅了一眼,而后顺着小儿子的视线,看到了立在堂屋门口的马谡。
强烈的惊喜陡然涌出,瞬间塞满胸腔,马夫人胸口剧烈的起伏着,快速丢掉竹板,含情脉脉的叫了一声“夫君”,而后羞涩的低下头……
静静等待着马谡勇猛的扑过来,抱住她,乃至扛起她,直奔里屋……
以前,每次出差回来,马谡都是如此做的。
蛮不讲理且英勇无敌。
那令人浮想联翩的久别胜新婚呀……
然而,这次似乎有所不同。
马夫人等了好一会,却什么都没等到,倒是听到长子马温怯怯的叫了一声“父亲”。
她失望的抬起头,看着从马谡背后缓缓出现的羌女,忽然间明白了什么。
门口守卫的传言,她不是没听到过。
她十六岁就嫁给马谡了,十六年来生了五胎,还都是男孩。这妇德,已经顶到天了。
最关键的是,她与马谡十几年如一日恩爱,感情基础坚如铁磐。
而且,32岁的她依旧风韵犹存。
诸多优势在手,是以,她对“马谡有新欢”的传言嗤之以鼻。
但是现在,这铁磐似乎一瞬间就碎成了渣,一同碎成了渣的,还有她的心。
“阿母,你怎么哭啦?”听到幼子稚嫩的声音,马夫人恍然回过神,抹了一把眼眶,发觉手心里晶莹一片。
她又看了眼那个不速之女,还有眼神极其陌生的夫君,弯腰抱起小儿子,快步逃向内室,趴在床榻上啜泣了起来。
眼泪如决堤般肆虐。
堂屋里。
马谡望着闻讯聚集过来的四个大小不一的男孩,闭上眼,努力给自己灌输了一百多遍“我有五个儿子,我是他们的爹”,而后睁开眼,进入父亲角色。
一一与他们见礼,询问他们的名字,年龄、学业及梦想。
还有家里的现状。
府里有多少个仆人?有多少个丫鬟?
四个男孩争先恐后的回答了所有问题,并附带着告诉了许多马谡未曾问道的问题。
丫鬟们年纪多大了、身材好不好、谁的身材最好、好不好看、谁最好看……
半个时辰后,马谡大概对“自己”的新家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
府里目前共有一百零六口人,即夫人和五个儿子,一个管事及其家人,十对男女仆从夫妇的家人,另外有五个年轻未婚女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