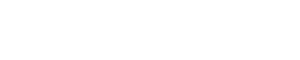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68节
作品:《三国从单骑入荆州开始精校版》盟主,咱荆州还是不要争了。”
刘表瞥了他一眼,似有不甘:“为父是这联盟的发起人,却要将盟主拱手相让?”
刘琦知道刘表只是一时之气,劝道:“父亲,其实您心里早就知道,这盟主无论是刘焉还是刘虞,都比您更有资格坐,咱们是争不过他们的。”
刘表的心情憋闷,但他知道刘琦说的是对的。
确实,他跟刘焉和刘虞是比不了的,因为那两个人各有优势。
刘虞的优势在于身份和功绩……论功绩,单是平定举纯之乱这一事,便足可秒杀刘表。
至于身份,刘虞的身份不仅仅是他大司马之职,还有他的出身。
刘焉和刘表的先祖鲁恭王是西汉王族,年代久远,且几经变迁,这一族目下在雒阳宗正府可查的都是支脉小宗,颇有些落魄皇族的意味……虽是宗亲,但血统都不是特别纯正。
多少带点串。
但刘虞的先祖乃是光武帝刘秀的嫡长子东海恭王刘疆,一度还曾当过太子,可谓根正苗红。
而刘焉的优势在于辈分和名望。
刘焉和刘表一样,都属名士,但刘表毕竟有因党锢之事而弃官逃亡的前科。
而刘焉年轻时曾拜名士祝恬为师,后党锢时,他没有选择和刘表一样与宦官决战,而是隐居自保,用七年的时间隐居教学,不但积攒了声望,还没有被牵连。
第二次党锢祸时,刘焉又当上了司徒胡广的文吏,搭了胡广的便车,他在司徒府镀金后外放,成功躲避了第二次党锢之祸。
刘焉这辈子左挪右闪,一直在想办法避开士族清流与宦官对决的主场,没有一次掉进过坑里,诚可谓是党锢之乱中的‘忍者神龟’。
也因为如此,他的政治底子相比与刘表就要来的干净些。
所以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,在三刘之中,刘表都没有成为盟主的可能性。
最不济,那俩人还是州牧呢,而他目下只是刺史……
“纵然如此,也不能推举刘君郎为盟主!此獠绝非善类。”刘表气愤地道。
刘琦闻言笑了。
“自然,依孩儿意,父亲与刘焉虚与委蛇便是,谁当盟主,也不是他刘焉一个人说了算的,大司马想来也会争上一争,父亲且先答应刘焉便是,待日后大司马派人问时,再虚应大司马,两不得罪,依孩儿想来,他们两人彼此谁也不会相让,最后基本就是拖黄了……咱们不慕虚名,只取其实。”
刘表眯起眼睛,斟酌半晌方道:“吾儿言之有理,深和朝堂之道,为父适才是有些急了,且先应了刘焉,待他出川之后,再做定论不迟。”
说罢,刘表转头问伊籍:“刘君郎还说了什么?”
“刘益州还言,川中多险路,且往关中之路不通,运粮极为周折,请使君供应其粮秣。”
这一次,刘表没有生气,他似乎已经想到了这一点。
“这老匹夫,真是算计到骨子里去了。”
刘表自持清流,既能说脏话骂刘焉为‘老匹夫’,足见其胸中对刘焉之愤慨。
伊籍在一旁道:“此事在下曾与刘益州力争过,但他绝不退让。”
刘琦暗道刘焉是吃定我们一定要促成这个联盟,当然不会放过揩油的机会。
“父亲,此事依旧权且应着,还是那句话,刘焉的五千兵将不出川,一切皆为惘然,可刘焉的兵将一旦出了益州,那便是无根之萍……”
说到这,刘琦笑了,他下话没继续说……
你用我荆州之粮,那我的粮秣便是你的命脉,我若要断你命脉,你再从蜀中往外运粮,还能赶得及么?
等川军出了益州,我要是真试着掐一掐你的粮草,你们要不要对我俯首听命?
或许在刘焉心中,刘表是汉室宗亲,又是清流名士,还是发起联盟之人,这样险恶之事他干不出来……
但他不知道刘表有个熊孩子。
……
就这样,刘焉那殊为过分的要求,刘表一样不差的全都应了。
随后,便是出兵往秭归会盟。
荆州军这一趟出兵的阵容,为襄阳校尉刘琦、别部司马黄忠,别部司马文聘,襄陵令蒯越,别部司马蔡勋等人。
因为蔡蒯两家人同时随军,因此两家亦是各出一千人马随行,共计七千人。
整整出动七千步卒,这对于仅仅控制了江夏郡和南郡的刘表来说,可谓是相当巨大的军事行动。
第五十九章 寻相熟之人引荐
益州,绵竹。
“君侯,江关都尉严镛之弟严颜,在府外拜见,想要拜见君侯。”
刘焉躺在软塌上,枕着卢夫人的大腿,闭着眼睛,正享受着卢夫人用耳勺为他采耳除垢。
听了管事的话,刘焉只是轻轻的‘嗯’了一声,随意:“让他在府外候着就是了。”
“诺。”
州牧府的管事走后,卢夫人轻轻地冲着刘焉的耳朵眼一吹,然后继续为刘焉采耳。
“君郎,那严颜到了绵竹已有一月,且每日来府求见,可你只是让他在府外候着,侯一天后又遣走他,从不召见……究竟为何?”
刘焉被采耳采的舒服的哼了一声,半晌后方才道:“打磨一下棱角而已,顺带敲打敲打,让他做到心中有数,晓得该为谁所用,这样才好赋以重任、委其大事,呵呵,严家人和其他益州豪族不同,一直都上进的紧。”
卢夫人奇道:“什么大事,还需要用到他一个江关的别部司马?”
刘焉没有吭声。
卢夫人知趣的闭了嘴,不再询问。
他们俩相处也有一年有余了,卢夫人对刘焉的秉性颇为了解。
别看刘焉对自己这般宠幸,但在真正的重大事宜上,刘焉一直是防备着自己的。
或者说,他防备着川中所有的人。
大概又过了两炷香的功夫,刘焉方才从卢夫人的大腿上起身,舒服的抻了个懒腰,笑道:“夫人,你该走了。”
刘焉很少主动让卢夫人离开,他要是这么说,一般就是有要事办。
卢夫人识趣地站起身,冲着刘焉盈盈一礼,便要离开。
“等会。”刘焉出言叫住她。
“嗯?”
“走后门。”刘焉微笑道。
卢夫人识趣的点了点头,出了暖阁后,便改道走后门出府。
待卢夫人走后,刘焉便招呼来了府中管事,对他道:“着严颜进来。”
“诺。”
过了不一会,府中管事便引着严颜走了进来。
严颜急忙对刘焉行礼道:“末将见过君侯!”
刘焉道:“严司马不必多礼,老夫近期公务繁忙,屡次想要接见于你,可惜一直未曾倒出时间,委屈你了。”
严颜心中很是苦涩。
自己来绵竹一个月了,几乎日日前来拜府,但刘焉一直不见他,摆明了就是故意为之,何来公务繁忙一说?
“君侯诸事缠身,日理万机,严颜能得君侯接见,实是荣幸之至。”
刘焉面色肃整,问道:“严司马从江关远来,滞留月余不走,不知有何要事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