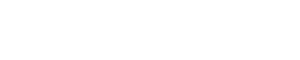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173节
作品:《我们生活在南京精校版》味倒也没那么拉胯。”
“单纯是因为这首歌没那么老罢了。”白杨翻白眼。
连翘不再说话,接着哼着她的调子。
白杨在心里补上歌词。
“因为梦见你离开,
我从哭泣中醒来,
看夜风吹过窗台,
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爱。”
公园里晨练的人逐渐多了,许多男男女女从湖边的小道上经过,冬日清晨澄澈冷冽的空气隐隐有小狗在叫。
“多少人曾爱慕你,
年轻的容颜,
可知谁愿承受岁月,
无情的变迁,
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,
来了又还,
可知一生有你,
我都陪在你身边。”
“哦对了,有件事得告诉你,今天是我带你晨练的最后一天啦,我的任务完成,也要撤离指挥部,昨天晚上调令就下来了。”连翘扭头对白杨说,“关系已经转走,我要归队了。”
“啊?”白杨愣了一下,这消息突如其来。
“你的特训结束了,白杨同志,你表现得很好,本辅导员给予你优秀学员的称号。”连翘笑眯眯地捏白杨的脸颊,“怎么?舍不得姐姐?”
白杨把头偏到一边去。
“嗯……舍不得。”
连翘用力拥抱他,“人生无不散之宴席,小白杨,跟你共事这段时间我非常快乐,分别总是会来的,但分别是为了下一次重聚,就像大小姐说的那样,我们也会再见的。”
她感觉到白杨的肩膀在微微发抖,于是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。
“别哭,你姐姐我耳根子软,看不得人哭,把眼泪擦干。”
“嗯。”
连翘后退一步,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,微微低头,嘿嘿一笑。
“那有没有临别礼物给我?”
白杨上下摸索一通,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温热的硬币,放到她的手心里。
“这是什么?”连翘仔细端详手里淡黄色的硬币,硬币表面刻着数字和字母,“如果我没记错,它是莫尔斯码练习币对吧?”
“嗯,它在我这里很长时间了。”白杨点点头,“送给你。”
“这个礼物很棒!”连翘喜笑颜开,喜滋滋地把它放进口袋里,“我会好好保管它的!”
连翘还是那么精力充沛,行动干练,她来得风风火火,走得干脆利落,白杨站在那儿目送她沿着小路越走越远,连翘走到很远很远,忽然转过身来,在温暖的晨光下站直了对他敬礼,笑容灿烂。曾经相聚的人们再将各奔东西,此生或许不复相见,怔忡许久,白杨泪水又模糊了眼眶。
后记
今年三月底,也就是在本作完结前夕,笔者受南京师范大学邀请赴宁参加活动,在活动间隙最后约见了一次赵博文。
老赵总是很忙,行色匆匆,仍然是那标志性的玳瑁框眼镜和深色风衣,与往次不同的是戴了副蓝色医用外科口罩,这阵子回南天又恰逢连绵阴雨,气温低得很,他把扣子系得高高的,手里拎着把黑伞,到我面前坐下。
“哎呀哎呀真是不消停啊,这见鬼的疫情一阵一阵的。”赵博文嘴里嘟嘟囔囔,“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。”
“南京最近还好吧?”我问。
“还过得去,没上海那么严重。”赵博文在椅子上坐下,摘下口罩,随手把壶里的茶给自己满上,都是老相识了,自然不客气。
我们约见在新街口路边的餐厅,靠着门口坐,到傍晚六点时外头下起蒙蒙细雨,很快路上五颜六色的伞就撑起来了。
寒暄几句,提及白震王宁等人的近况,赵博文表示这些老梆子一个个活得可都滋润着呢,丝毫不受影响,老白照旧在花心思改造他老家鹿楼镇的房子,定期回去监工,王宁最近被抓去当防疫志愿者,忙到腿抽筋,整天骂骂咧咧,上级表示过要提拔他,不过他拒绝了——经此一役,老王对自身的能力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,他知道自己不是当厅长的料,于是向上推荐了小朱。
至于赵博文自己,他对自己最近的工作缄口不言,当笔者问起此事是否还有后续时,他也就是神秘一笑,笑得意味深长。
看到这副表情,我就心知肚明——大工程是有,不足为外人道,以后在新闻上看到什么都别吃惊。
“喏,这是稿子,你审核审核。”我从背包里取出厚厚一叠打印的稿纸,扔在餐桌上,“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,尽管提。”
赵博文把它拿过去翻了翻,摇摇头:“不必给我看这个,我一直追着你的连载呢,你更一章我看一章,还在你的评论区里发表过评论。”
“哪个是你?”
“保密。”老赵说。
“那你有什么建议?”我问。
“没什么建议,我不懂文学创作,我提看法就是外行指导内行。”老赵笑了笑,把手里的稿纸拍在桌上,“我很佩服你写得这么详细还能对得上,到时候真误导了读者去月牙湖捞时间胶囊怎么办?实际上胶囊又不在那儿。”
“月牙湖那么大,捞不着的。”
“你到时候出版就用这个吗?”老赵指指桌上的稿纸,“还会做什么大修改不?”
“嗯,用这个,不改。”
“所以……最后还是决定给她起名叫半夏?”
“是啊,她总得有个名字吧?还是说你对这个名字不满意?”
“不不不,我很满意,这个名字很好,指挥部里一直叫代号,杨杨他们叫她大小姐,也有人给她起过名字,都没你这个好听。”赵博文说,“她应当有一个很好的名字。”
“在一个只剩下两个人甚至一个人的世界里,名字有什么意义?”我说。
“名字是你在人们记忆里的锚点,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痕迹。”赵博文说,“没有名字的人就像风一样,一吹就消失了。”
“时间过得可真快,一晃快两年过去了。”我说,“按照年龄算,那姑娘应该出生了。”
赵博文想了想,点点头:
“嗯,2040年她19岁,2021年出生,现在可能才刚刚一岁。”
“赵老师。”
“嗯?”
“她还活着么?”
“我相信她还活着,虽然不可能求证,但我愿意相信,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塑造现实,天瑞老师,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委托你写这本书,如今我们的未来已经重新回到了黑箱里,她会有一个不同的未来,或者说我们可以为她创造出一个不同的未来。”赵博文目光遥远,“这一直是我们所希望的,也是我们所努力的。”
“任重道远。”
“这世间万事万物,包括我们整个物质世界,在最底层上都可以视为信息,信息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,它是可以影响周围世界的,物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功,那么信息是有能力对外做功的。”赵博文说,“我们不应当把信息传递与物质变化分割开来看待,站在我们的角度上,未来是什么样,取决于我们观测到的结果,当我们失去唯一一个观测者,而那些未被观测到的黑箱,就蕴含着无限可能。”
“有十足把握?”我问。
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