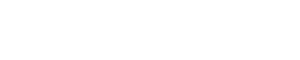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53节
作品:《新书精校版》叫住了他:“我倒是对子云翁昨日一显神通,却没有列入这些得意之作的《方言》,有些兴趣!”
听到这扬雄却是一愣。
除了想要“报恩”不欠人情外,扬雄对第五伦其实是有些喜爱的,毕竟第一印象太好。
他家五代单传,传到扬雄时,两个儿子又同时死去,尤其是最聪慧的小儿子扬信。9岁时就能和扬雄辩谈那本以艰深而著称的《太玄》,竟也早早离世,让扬雄痛不欲生。
而侯芭虽然勤勉,但才学不高,对扬雄最得意的《太玄》《法言》理解有限。王隆等人,则只对扬雄早就自我厌恶的辞赋感兴趣。
若是能再收位有天赋的好弟子,将这些耗费了他一生心血的学问传下去,就好了!
却不料,第五伦只对他最冷僻学问有意向。
这方言一书,全称是《輶(yóu)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。
据说周、秦时期,每年八月会派遣輶轩之使,到各地采集异代方言,收集整理之后,收藏起来,便于考察天下风俗。
秦朝灭亡,这些文献散落殆尽。像前朝刘向这样的大儒,也只闻其名,而不详其职。
倒是扬雄在蜀中时的老师严君平记诵千言,略知梗概。扬雄从学,并以此为基础,积三十年之功,终于收录天下各处方言于一书。
在时人看来,这是不入流的杂学,连扬雄也觉得,这不过是自己兴趣所在,为了完成师长夙愿而作,乃是悬诸日月,不刊之书。等自己死了,送入石渠阁收藏即可。
殊不知,第五伦倒是觉得,扬雄方才列举了种种学识,都没什么用处。
辞赋作得好又如何,给王莽再写一篇剧秦美新?至于什么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,光听名字第五伦就没兴趣。易经和论语第五伦晓得,但扬雄仿照体例所作的两本书,恕他历史不好,根本没听过啊。
第五伦暗道:“应该只是扬雄的自嗨之作,后世要么失传,要么束之高阁了,一定是这样。”
他时间精力有限,不能用于实际的知识,诸如繁杂的章句训诂,第五伦是不会去学的。
但方言这项技能,第五伦有兴趣尝试一下。
第五伦之所以来常安,一是为了见识下王莽的“新朝雅政”究竟是如何闹得天下大乱,二是想与国师“刘秀”会一会。第三嘛,则是想在人物荟萃的京师结交四方豪杰,以待他日之用。
但这两天在郎署里,跟来自各州郡的孝廉们相处一番后,第五伦发现,大家光是想好好说话沟通都很难。
这年头十里不同音是常事,若是相隔千里,彼此方言基本就完全听不懂了。确实有洛音雅言作为“普通话”,但这年头没有拼音字母,随着时间推移,雅言本身都在产生偏差。就更别提因人而异,有的人不说雅言还好,一说你会发现……
“他还不如说方言呢!”
正因如此,数百人的郎官中,除了萧言与一帮前朝遗少自成一派外,基本都按地域分出不同圈子,彼此交流很少。
音韵相通是最简单的结交理由,谁会跟彼此无法交流的外乡人交朋友呢?
反正闲着也闲着,倒不如跟扬雄将这方言之术粗略了解下,多一项技能好过没有,以后可以说一句:没人比我更懂方言。
最起码,夸人和骂人的话得知道。
见扬雄久久不言,第五伦笑道:“莫非子云翁不舍得?”
“非也。”扬雄摇头:“只是想起,伯鱼是第二位对这学问有兴趣的人。”
“哦?第一位是谁?”
“当朝国师,刘子骏。”扬雄露出了苦笑,不再想提这件事,他还是习惯称呼国师曾经的名字:刘歆。
二人一起做过黄门郎,曾是莫逆之交,一起交流学问,抨击前朝成哀的黑暗政治,又同时被周身散发着儒家理想之光,俨然周公再世的王莽吸引住,甘心受他驱使。
但随着年纪渐长,随着新室的种种弊病显现,二人理念相左,居然反目成仇了。
刘歆曾嘲笑扬雄自苦创作,说他所写的简牍文书,以后要成绝响,世人不会理解,而要拿去当酱缸的盖子。
可刘歆又觊觎扬雄的《方言》,随着前年刘歆写信威胁索要,而扬雄回信说出了“缢死以从命”这样的话后,二人彻底闹掰,自那之后再无往来。
扬雄不愿再多提及老友,只打起精神来,开始给第五伦传授学问。
他前脚才支使王隆去翻阅辞赋自学,对第五伦却极上心,找来藏在家中的方言一书,耐心地说教。
“这天下方言,大致可分为十四区域。”
“秦晋为一系,梁及西楚为一系,赵魏自河以北为一系,宋卫及河内为一系,郑韩周自为一系……”
……
常安城郊的太学区舍处,刚来报到,准备在此游学一年半载的刘秀,正在面临一场刁难。
“你这前队人,名字叫甚么不好,偏要叫刘秀!这不是让吾等为难么。”
来为他们登记名册的博士弟子趾高气扬,手持木牍毛笔,对刘秀、邓禹等人呵斥起来。
前队,是王莽更改的南阳新名,南阳人都觉得难听无比,好好的南方大都会,一下子变成里闾小村的感觉。
可却又没办法,与他们同病相怜的还有河东、河内、弘农、河南、颖川,六个难兄难弟被凑成了王莽的“六队郡”,紧紧围绕着改名为“保忠信卿”的洛阳城。
但刘秀万万没想到,新室改名居然改到自己头上来了。
原因无他,博士弟子说,国师公就叫“刘秀”,二人重名了,于是他要求,刘秀平日里爱怎么叫怎么叫,却得重新想个名记在薄册上。
邓禹年少英才,有些不服,辩驳道:“只听闻天子登位,布名于天下,四海之内,无不咸避,却没听说过要为四辅三公避讳啊。”
听说国师公原名刘歆,正是为了避汉哀帝的同音名,才在二十年前改称“刘秀”。
如今却是少年变恶龙,要将改名强加到别人身上了。
邓禹还是嫩了些,论掌故,哪里敌得过这些博士弟子,却见那弟子冷笑道:“前汉时还真有为外戚避讳的,禁中者,门户有禁,非侍御者不得入,故曰禁中。新室文母太后之父,大司马阳平侯名禁,当时避之,故从此以后皆曰省中。”
“如今国师公嫁女予太子,也算外戚,避讳情理之中,一字尚且要改,何况你是姓名一齐撞了。”
“再者,太学中不少博士皆是国师公高徒,若是他们拿着薄册念名,读到‘刘秀’二字,岂不是直呼师长尊讳,是大不敬了?休得多言,速速想个写上去,往后在太学中,你也多称字,少说名。”
这一席话,让素来谨厚的刘秀都忍不住捏了捏拳头。
他这名,是亡父取的,是岁县界有嘉禾生,一茎九穗,因名曰秀。出生后三个月,告于舂陵祖庙,让祖先知晓,岂能随意改动,哪怕只是临时。
若换了刘秀的长兄刘伯升在,肯定大骂“这太学不上也罢”,拂袖而走,继续琢磨他的复汉大计去了。
但刘秀不同,他的冷静能够胜过愤怒,终究还是松开了手,接过了笔。
但要落下时却又犹豫了,写什么呢?刘文叔?但在一堆单字名里,二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