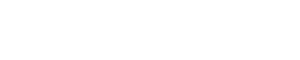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116节
作品:《明朝败家子精校版》不嫌……”
他不甘心啊。
方继藩恼了:“说不要就不要,原本一个江臣,会试才将将考了第八,便教我没脸见人,无地自容了……”
站在一旁的江臣,像是被一把刀子戳在了心口。
方继藩露出抱歉的样子,看向江臣道:“小江,为师说话比较耿直,你不会介意吧?”
江臣眼里朦胧,似有雾水,就差哇的一声哭出来,却努力地摇了摇头道:“不介意,不介意。”
方继藩颔首点头,才向徐经道:“你看,一个江臣,我方继藩便已觉得可耻,丢人现眼了,你自己说说,你考了第几?”
“……”徐经不禁一脸羞愧。
他考的更差,二十多名。
虽然会试二十多名,而且以徐经的年纪,殿试只要表现尚可,十拿九稳是二甲进士,而且他长得不错,大明的授官,是以貌取人的,现在虽是在狱中被打的面目全非,可到了那个时候,大抵也能恢复他英俊的相貌了,进翰林院也是十拿九稳。
这样的人,放在全天下,那都是未来前途远大的翰林官,可到了方继藩这儿,他竟有些抬不起头来了。
徐经还是想再争取一番,便道:“学生自幼爱读书,家祖徐讳颐、家父讳元献,都曾是江南大儒……”
徐经似乎觉得,这已是他唯一拿的手的东西了。
他出自名门,梧塍徐氏,在明初时可是名噪一时,声名远播。
方继藩则是笑了:“你祖父和你父亲,于你何干?”
徐经更是羞愧得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了,只好深吸一口气道:“学生在吾祖吾父熏陶之下,自幼酷爱诗书,乐学不倦。一切家计都由家母和贱内操持,自己则埋头于举业。平时足不出闾,目不窥市。”
方继藩很不给面子的一脸鄙视道:“书呆子而已。”
“……”
原本这些东西,对于一个读书人而言,可都是很自傲的东西,爱读书,家里有名望,哪一样不是很有牌面的事?
可方继藩却都不屑于顾。
徐经眼睛发红了,一直跪在地上不肯起来,他不甘心啊,这个世上,还有徐经拜不着的师?以往不知又多少人死乞白赖的想要收他进入门墙啊。
他深吸一口气,想了想,觉得恩公是非常人,既然不喜欢书呆子,那么……他定定神,便道:“学生家富藏书,家中所筑‘万卷楼’中藏有大批从宋、元两代兵荒马乱中幸存下业的古文献。其中有不少天文、地理、游记之类的著作。学生自幼,便讲其牢记于心,四书五经,对学生而言,不过是举业而已,天文地理,经史古籍,学生无一不知。”
这是他的杀手锏了。
其实关于这一点,他没有吹牛。
徐家在南宋时起,就已是大儒世家了,徐经的祖父们,曾搜罗无数古文献,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史上,徐经的孙子徐霞客,被称之为中国地理学家,这是有家学渊源的。
方继藩有心要挫一挫徐经,只是冷笑:“天文地理,能吃吗?”
“……”
此时的徐经,悲愤得想死了。
方继藩便道:“你的水平,做我的徒孙都不够,我已有一个劣徒江臣,拜师之事,不要再提了。”
江臣:“……”
杨管事在旁看得眼睛都发直了,只是少爷在说话,他不敢插嘴,怕在外人面前丢了少爷的面子,只是……他在心里捶胸跌足,少爷啊少爷,这么好的一个青年才俊,想要拜在你的脚下,何必要这般的折辱他。
心里感慨又惆怅,忍不住扫了一眼唐寅、欧阳志人等,不免又耿耿于怀,现在的读书人,脑壳都坏了,都坏了啊。
当天夜里,徐经一脸的苦涩,他已收拾好了行囊,预备明日便搬出去,他和唐寅在一个房里住着,临别在即,这一尘不染的书楼里,一盏青灯冉冉,照耀在徐经伤痕累累的脸上。
他一声长叹,很有不甘,接着,他苦涩摇头道:“伯虎,有时候真羡慕你,恩公这样的人,虽然说话太直接,出口如刀,却是有大智大勇之人,外人如何看待他,这不重要。可于我徐经而言,若能拜入他的门墙,就算不从他身上学习到什么道理,可即便能侍奉他,心里也甘愿。”
徐经对方继藩,是存着万千感激的。
当初,他惹的事,太大了。
徐家乃是江南名门,在京师不是没有关系,可自牵涉到了舞弊,下了诏狱之后,那些平日里在京中的故旧,却都惶恐不安,没有一个人敢出手帮衬。
其实,徐经不怪他们,要怪也真怪不来,如此钦案,谁碰谁死,即便是至亲,怕也只能发出一声悲鸣罢了。
可唐寅求到方继藩头上,方继藩居然满口答应了。
作为唐寅的恩师,方继藩就因为徐经是唐寅的朋友,居然就挺身而出了。
你看,这样的恩师,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啊。
不只如此,方继藩还把事办成了。不但让徐经活着走出了诏狱,还恢复了徐经的功名,甚至……天子下了罪己诏书。
这不是大智大勇又是什么?
第0114章 金玉良言
徐经想要拜师,一方面,是他和唐寅乃是至交,二人若能成为同门师兄弟,那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另一方面,也是因为他敬佩方继藩的为人。当然……是敬佩方继藩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东西,而不是那种满口粗鄙之语。
可怎么没想到,最后方继藩竟是拒绝要他这个徒弟。
看着徐经失望之极的脸色,唐寅终于忍不住道:“徐兄为何要放弃呢?其实恩师是个心软的人,只要徐兄坚持,恩师一定会答应的。”
徐经不由苦笑,冉冉的烛火照在他的脸上,更显落寞:“我何尝想要放弃,只是……不得其法罢了,恩公这般嫌弃我,我若是还死乞白赖,岂不是成了天下人的笑柄?”
说到底,还是他的家世以及骨子里的傲气作怪,死要面子,平时装逼装习惯了,现在承受不了天天被人打脸。
唐寅便劝道:“其实,也不是没有办法。”
“嗯?”徐经一愣,像是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。
唐寅道:“我听欧阳志几位师兄说起一事,恩师就曾靠着这个,乖乖让府中的人就范,既然他可以用此来强迫方家的人,那么恩师毕竟是心软的人。或许徐兄也可以试一试。只不过这件事,还需欧阳志三位师兄配合才好,只是这欧阳志三位师兄,似乎对愚弟有些成见……”
唐寅是个很有才情的人,只是做人方面,似乎差了一些。
更何况恩师显然对唐寅作画很有兴趣,隔三岔五便夸奖他,唐寅动力很足,现在在他的房里,摆着许多还未完工的画作,而欧阳志三人则是挨骂的比较多,多多少少,心里会泛酸水,此乃人之常情。
徐经却是一笑,他对唐寅有所了解,自是明白唐寅的意思。
不过这等打交道交朋友的事,却是徐经这等世家子弟最擅长的:“这个容易,交友最紧要的是折节,我看欧阳志三位同年,亦是老实本分的人,要熟络起来,倒也容易。”
这里灯影摇曳,唐徐二人,半宿不睡,低声在谋划着什么。
次日方继藩命邓健去詹事府告假,就说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