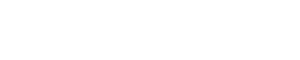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163节
作品:《新顺1730精校版》刺找茬,笑道:“连累他人,这话说的是有理的。当日我看到热气球飞到半空,便知你翼国公府定是鸡犬不宁。只是他既一心为国,便是再乖张十倍,朕也容得下。论及慧眼,朕与卿都不如齐国公,他是看出来子侄辈里可堪用的就这么一个。”
刘盛道:“齐国公当年去过福建,见识过西洋大船、火器之利。所以他以为将来必是要变革的,不过犬子恰好学西洋学问而已。齐国公又不言语,那日却把犬子骗去。也是陛下慧眼识珠,让犬子北行,方有尺寸之功。”
“哦,听卿之意,卿也认为西洋兵制是正途?”
“臣不懂西洋学问。既不懂,又怎么敢说是正途邪途呢?齐国公也未必懂,只是被西洋舰船震撼,心中觉得大约是正途。至于是否是,尚且难说。犬子也说过,北疆的罗刹人,非是罗刹京营,战力不强。”
李淦点点头,认可必须真的懂了才能说正途邪途的说法。
“齐国公奏书,说是罗刹国使团意图演练西洋阵法、炮术。朕觉得,此意在于示威演武。不过亦可一看。前朝澳门的葡萄牙人曾来京城演炮,结果炸膛了,那是为了卖炮。罗刹人此番自然不是为了卖枪卖炮,而是为了彰显武力。朕准备拟定一些人去观其演练。卿以为如何?”
刘盛笑道:“臣倒是想起来个笑话。一牛,拴在牡丹园、四月,正绽。三日后问之,牡丹若何?其曰:味苦且涩,弗如麦草远甚。”
李淦也笑了,刘盛又道:“如陛下真想改革军制,变革即可。若陛下希望群臣支持,不过一次演练,又能看出多少妙处?况且,朝中知兵者几人?戏林有云,台上一刻,台下十年。纵然观摩了罗刹军阵炮术,若不知其如何训练,也是无用。”
“古人云,举贤不避亲。若陛下有变革军阵之心,不妨以犬子一试。至于让罗刹示威演武,大可不必。至于我朝大阅以威慑,亦可不必。京营虽可战,但犬子说,京营战法若是大阅,反倒让罗刹轻视。”
他虽平日里不问政事,但真正关系到自己家人和对外交涉的时候,还是要说一句的。
李淦失笑道:“在他看来,国朝军阵已经落后许多。说起这个,朕心甚慰,前些日子他一直往罗刹俘虏那走动,多询问一些军阵细节。罗刹俘虏在那数月,除他之外,竟再无别人去。至于法兰西国、英圭黎国,涉及太多,诸如海关、关税、贸易等等事。若想学一学西洋战法,似也只能从罗刹那里入手了。”
“他既为勋卫,本该入殿前轮值。朕放他回去,不过是让他准备武德宫的夏考。但朕见他整日胡闹,看来是志在必得了,这免值之事也可免了。”
“正好,罗刹使团要了,他便在朕身边,做通译之事。一来朝中传教士所信天主而非东正,恐有私心;二来朕也正要知道更多的罗刹国事,也好做谈判之用,用以震慑。”
“自明日起,他就不要在家里无事生非胡闹了,就去殿前执勤吧。”
刘盛心头大喜,能够在皇帝身边做近身勋卫,那正是将来重用的一个表现。和袭爵的勋卫一样,做勋卫,那是做皇帝的身边人,让皇帝对你有所了解,日后才敢用。毕竟亲近。
这样一个机会,当真求之不得。这顿饭虽然吃起来没什么滋味,可却大值。
饭毕临行,李淦又笑道:“他带头胡闹,朕罚了一起胡闹的人银钱。这钱,总不好叫别人出吧?人家帮着你儿子去闹事,你可别连这千百两银子都舍不得,日后面上也不好看。还有,那陈震的事,就到此为止吧。热血少年胡闹而已,并无深意。”
“是。臣记下了。”
刘盛当然不信没有人背后指使挑唆,但皇帝都这样说了,就算有也是没有了。
第112章 小人哉
廷议还在进行中的时候,陈震被苌弘社中的几名元老叫到了无人处。
直到被叫走之前,他还在享受着那份无人的无上快意:让蛮子一样的武将折服、服以大义,而且还上演了史书里的故事,负荆请罪。
他以为自己被社中大佬叫走是要夸奖。
然而,社中的几位大佬劈头盖脸地将他一顿臭骂。
“你都和那刘钰说了什么?”
“那些话是你该说的吗?你说的这些东西,可有丝毫用处?幼稚之言,夸夸其谈,堕尽我苌弘社的脸面,折却天下读书人的体面!”
痛骂之后,陈震茫然无措,奇道:“诸位师长,我可是做错了什么?”
那几个社中素有声望的大佬们拿出誊抄的奏疏,将刘钰所记录的原话和借题发挥的内容复述了几段后,厉声问道:“这是你说的吗?”
陈震愕然,随后道:“是我说的。可我说的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,是刘守常他理解错了。我是说过,自宋之后,儒生多有妇女之态。可这也不是我说的,而是习斋先生所言。”
“况且,我也没说儒生应该去边塞历练,只是说……”
刚解释了半句,剩下的解释就被粗暴地打断。
“够了!”
“蠢货!”
“你知不知道你说这些,可能会带来什么?”
陈震是个心念坚定的人,自己认为对的东西,宁可死也不会弯折。听到社团长辈们的斥责,虽然按照礼仪,晚辈被训斥的时候不能还嘴,可终究还是忍不住了。
“刘守常所言虽然极端,可也未必没有道理。唐时儒生,提三尺剑纵横边塞,壮阔诗篇。至于更早,汉之班定远,文能做史、武能击匈奴。乃至后世,辛稼轩、陈同甫等辈,皆可马战持剑、文斗赋诗。”
“我辈儒生,若想洗却程朱妇女之态,就该复先秦之儒!刘守常所言,也未尝没有道理,若是我辈儒生若想进学,就必须要去边塞历练教化……”
正引经据典地便捷,早已经暴怒的社团长老大怒,骂道:“蠢货!蠢货!”
两句蠢货加身,陈震低着头,脖子却不肯前倾,梗着脖子道:“之前陛下破罗刹,诸位也不是与我一同联诗,恨不能饮醉沙场沙场吗?”
“如今朝廷拓边,四夷多服,就该让其服教化而尊名教,使之知德。”
这句话不说还好,一说,社中大佬更是骂道:“饮醉沙场,却不是去做那等寒酸之职。”
“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,彼其不悍然执兵,以与我従事于边鄙,则已幸矣!譬若禽兽然,求其大治,必至于大乱。蛮夷臣服于武力,不主动来打我们,就已经是幸事了,那种禽兽样的人,如果想要教化他们以求大治,只会引来大乱!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?”
“天下士子苦学十年,难道是为了去边塞吃沙土的吗?各司其职,各司其职,我等文士,就该壮文华而著文章。你如此说,要置天下士子于何地?”
“难不成这世上就只有你陈长公是真儒生,其余人都是假儒生吗?你说这样的话,又让天下士人如何看待我苌弘社?又为我苌弘社引来多少指责?”
陈震只觉得心头酸楚,握着拳头,用尽心中的正气问道:“我等以苌弘为社名。古人云:碧出苌弘之血,鸟生杜宇之魄!既要一腔热血化碧,难道连边塞风沙都忍不得吗?”
他的声音极大,已经带出了几分怨气和怒气,再加上捏紧的拳头,连声的质问,更让那几位他曾尊重的社团前辈气不打一处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