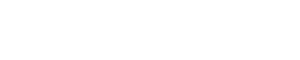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37节
作品:《新顺1730精校版》事的大顺决策层已经定下来了对策,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。
齐国公去接待罗刹使团,用礼仪问题扯皮。
围绕着东北事,要做的很多。
辽东继续修建驿站、囤积粮草。
遣派人去朝鲜,征调朝鲜的一部分火枪手,一则减少开支,二则看看朝鲜的态度,三则查看下朝鲜的军备。
京营的炮兵,也要趁着田索和罗刹人扯皮扯出的时间,秘密将大炮运送到松花江。
吉林造船厂抓紧时间造船,征调福建郑氏遗留的跳帮战精锐,剑盾兵、藤牌兵,急速北上,充实松花江的水师实力。
一旦时机来临,集结兵力,对罗刹国发起北征。
让北边的一些骑墙的蒙古部落正确地选边站,以免出现明末东虏之祸。
同时以大黄、茶叶贸易为要挟,迫使罗刹国不得干涉西北对准噶尔的战事。
东北战事一了,立刻征调松花江畔各个折冲府的精锐府兵轻骑,前往西北。
先东北、后西北。大略已定。
刘钰要带着一群人,先行秘密前往松花江畔。
以大黄走私贩子的身份,配合一些伪装成鄂温克部猎鹿部落的归化索伦人,查探罗刹城堡布防、沿河通行状况,绘制松花江、黑龙江各处的地图。
以及……拓永乐年间的永宁寺碑文,为日后谈判用。
朝中的人不是疯子,也不是傻子,能做到决策层如天佑殿的人,哪一个都会算经济账。
和罗刹国只能边打边谈,相隔万里,与西北边使使劲儿就能犁庭扫穴的准噶尔不同。
东北苦寒,又有松辽分水岭阻隔。
长久驻军数万,或者持续一场数年的战争,朝廷根本负担不起。
也就是从二十年前,小冰期过去,天气渐渐转暖,那地方才能种一点粮食。
以往,那里被称之为“犬国”,倒不是侮辱性的称呼,而是因为那里的部落驯养驼鹿、猎狗,冬日里靠驼鹿猎狗狩猎。
地瓜土豆玉米自明末传入中国,都以为那东西是神器,可放在此时的松花江畔根本不适应。
后世歌里唱的很准,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”,而不是“漫山遍野的玉米大豆”。
在玉米育种技术进步前,无霜期超短的松花江平原根本种不了玉米,只能种高粱大豆。
而大豆这东西……即便后世技术进步,化肥像是不要钱一样的撒,一亩地也不过400斤。
松嫩,不是辽东。
如果那地方真的如一些人幻想的那般是适宜耕种区,以诸夏对可耕种土地的渴望,岂能空白数百年?
北大荒,没有大型拖拉机之前,只能是北大荒。
闯关东,没有横贯南北的铁路越过松辽分水岭钱,只能闯到辽北。
松嫩三江,漫地的沼泽,没有抽水机,种不了地。
半米深的草根,虬髯错节,链轨拖拉机将将能够破开草根,牛马累死也耕不动。
多年淤积的沼泽水,没有深水机井,得了鼠疫而不死的黄鼠到处都是,吸了血从小米大小暴涨到指头肚大小的蜱虫,能爬满猫狗身躯如同克苏鲁生物满身瘤疣。各种稀奇古怪的病,克山病、风口症、出血热、鼠疫、克汀病、森林脑炎。
牛虻马蝇蚊子小咬蜱虫,数不尽的吸血飞虫,采金人对付私藏金子的同伙,只需要剥光了衣服,用不了一天就是一具皮包枯骨。
八月十五飞大雪、清明踏青冰未融、七夕冰雹时常事、腊月寒风入骨髓——这才是那片黑土地此时的真正模样。
从甲申年崇祯上吊开始算,开国八十年,战乱乱了几十年,真正休养生息也没几年。
辽东的人口明末大乱之后,几乎空了。当年大顺在辽东扫穴犁庭,四个字,不知多少尸首。
如今辽东都填不满,更不会有人“明知北方苦,偏向北方行”。
越过松辽分水岭去松花江水系的,寥寥无几,最多也就是些采金、猎皮的。
战争是政治的延续。
打完了,最终还得谈判解决。而谈判除了要靠武力,还要靠“自古以来”。
好在永乐皇帝留了些遗产,朝廷有自己的底线。
本来李淦继位之后,就想着解决东北、西北的边患。最开始也是希望借传教士帮忙,去东北绘制精确的地图。
谈判时候,己方连地图都没有,气势上就会先输一截。
可如今和传教士闹翻了,之前还抓过传教士私传地图去澳门这种事,实难信任。诸夏没几张此时欧洲的地图,欧洲却遍地都是传教士偷偷带回去的带经纬度的中国地图。钦天监、职方司里一群传教士,山川关隘对西方毫无秘密可言。
这件事又属机密,勋贵圈子里唯一懂西学的,也就是刘钰了。
这差事,是个苦差。
甚至有些九死一生的意思:如今大顺在松花江畔最东北的边堡,在后世的依兰县,距离松花江汇合黑龙江处还有三五百里,更别提永宁寺碑更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。
为了防备罗刹人提防,不能乘船,也没法乘船。
要靠沿途的各个部落接应,愣生生走到那里。
要伪装成猎鹿的鄂温克部落;伪装成走私大黄的商人,去打探罗刹城堡的布防情况。
要和沿途遇到的各个部落结好关系,记录沿途山川,更要询问各个部落对于罗刹国征收“牙萨克”毛皮税的不满程度。
虽不及张博望通西域,却也并不容易,九死一生也非只是个形容。
在皇帝面前,刘盛唯唯诺诺;在田索面前,刘盛重拳出击。
毕竟那是自己骨肉,摊上这么一件九死一生的差事。
一肚子的邪火不敢在紫禁城里发出来,只能回到家对着田索摔盘子砸碗,以示自己的愤怒。
勋贵子弟的路,没必要走的这么难。
就算是说去军前效力,历练经验,勋贵子弟哪里需要这样历练?
镇守西南改土归流的,是襄国公,那是刘钰的亲舅舅;西北边战事不断,大军云集,最容易立功,虽然在那边任权将军的不是勋贵圈子里的人,当年在武德宫还曾口吐狂言对勋贵子弟纨绔之流颇为不满,可至少安全些。
刘盛早就知道刘钰偷偷摸摸和齐国公鼓捣《西洋诸国略考》的事,他之前并不阻挠,因为他觉得这是好事。
简在帝心,或者跟随齐国公去和罗刹使团接洽,都是镀金的好出路。
镀金镀金,既无危险,又长资历。
哪曾想皇帝雄心壮志,竟是一下子把自家儿子扔去了三千里白山黑水间。
这哪是镀金?
这是真刀真枪的上啊。
田索估摸着刘盛的气也撒的差不多了,弹了一下茶盅,幽幽道:“刘兄,你以为次子封勋卫,那是随便封的?国朝开国至今,非袭爵嫡长封勋卫的,有几个?真以为勋卫是散骑舍人这样的烂大街大白菜?”
“别在这发无名火了。把老三叫过来吧,该嘱咐的事嘱咐一下。如今已是八月了,腊月前就得出发了。”
刘盛跟着叹了口气,知道这件事只能如此。
就要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