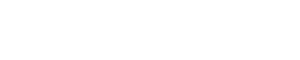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8节
作品:《从解除人体限制开始精校版》到有人躺在地上。”
路边的一辆海鲜运送货车前,一个四十多岁,满脸沧桑的鱼贩子,正在向两个警察做现场笔录。
“大概是在几点钟?”其中一个女警询问道。
“我一般离开市场那边的时候是四点半,开过来……”那个中年鱼贩子挠了挠头,突然比划了一下手指,“五点,差不多是五点。”
“这么早就送货呢?”
女警旁边的一个便衣,咧了咧嘴,颇有些不信道,“鱼市都还没开吧……”
“阿Sir,哪里早了,我要跑荃湾、新界,还要过海呢……”中年鱼贩急忙解释道。
“蛮牛,你不懂就少说几句。”
女警白了一眼身旁的便衣一眼,停下了手里的笔,目光盯着这个送海鲜的鱼贩子问道,“那你经过的时候,有没有看到其他人?”
鱼贩子被女警盯得有些慌乱,连忙摇头道:“没有啊,这段路大早上没什么人的,长官,真的是我报的警……”
嗡嗡——
就在这个中年人说话间,一阵引擎的咆哮声响起。
一辆丰田轿车在警戒线前停了下来,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,在他副驾还坐一个体态妖娆的美女。
“哇,正点啊。李Sir这是又换新伴了。”
那个叫做蛮牛的便衣看着丰田轿车上的那个美女,眼睛睁大,露出了一副艳羡的表情。
“好好做事啦。”
旁边的女警同样注意到了副驾上坐着的那位美女,有些生气地用手肘撞了一下叫做蛮牛的便衣,又小跑着走到了那中年西装男子的面前。
“阿bo,情况怎么样了?”
从车上下来的西装中年男子,环视了一眼现场,看着走到面前的女警随意问道。
“李Sir,我们已经查到了,死者名叫林过雨,是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。我们在出租车旁找到一把三十公分长的剔骨刀,不过死者身上没有伤口。前面鉴定组的同事说,死者是受到巨力撞击引发的肋骨断裂,刺穿了心脏和肺部,导致的内部大出血引起的死亡。”
被称作阿bo的女警,站在西装中年男子面前,一板一眼的汇报道。
“被撞了?”西装中年男子漫不经心地问了句。
“不是,鉴定组的同事说现场没有车辆行驶撞击的痕迹,如果是被车撞的话,现场应该能找到点什么的。而且从昨晚到凌晨一直在下雨,我们在现场的那把剔骨刀上也没办法提取指纹。”
女警阿bo摇了摇头,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,“对了,李Sir,前面有媒体过来了,要不要通报给媒体啊?”
“你想引起全港出租车罢工啊?”西装中年男子瞥了一眼女警阿bo,“先不说,实在不行的话,就说出租车司机中途下车,被后面上来的车撞了。”
“那……那我们不查了?”女警阿bo有些茫然地问道。
“当然要查。”
西装中年男子没好气地说了一句,“这明显是杀人案啊,傻乎乎的,行了,我走了。”
“对了——”
西装中年男子离开前,又补充了一句,“找一找附近有没有目击者,从死者的死亡时间推断,前后公路上看看有没有人看到什么。”
“Yes Sir!”女警阿BO连忙应声道。
“哇,李Sir真是太潇洒了。”
看着丰田轿车离去,那个叫做蛮牛的警察走到阿bo身旁,满是羡慕道。
“做事啦!”阿bo狠狠将手里的笔录扔给了对方。
“干嘛?!李Sir不待见你,也别拿我出气啊!”蛮牛看着阿bo的模样,不由叫嚷道。
“你是没见过李Sir以前有多厉害!”
阿bo回头剜了蛮牛一眼,胸腹起伏,似乎依旧有些气闷。
“喋血神探嘛,谁不知道似的。”
蛮牛撇了撇嘴。
“Madam!”
正在这时,一个军装警快步朝两人跑了过来,“刚有家属报案,说他们的女儿昨晚被一个出租车司机绑架。”
……
距离青龙码头不远的龙腾街,不算宽阔的街道两侧,店面林立。
以港岛的人口密度来说,哪怕是在青龙头码头这边算不得繁华的区域,因为依托码头的分流,依旧有着大量的人口汇聚。
上午的时候,正是街道上最为忙碌的时刻,小商店前有人在高声降价,五金店里不时传出切割的声音,餐饮店门前热气腾腾。
各种广告牌下方的人行道上,往来有衣着光鲜的职场人士,有穿着汗衫拖鞋的搬运着各种货物的工人,以及抱着纸皮脚步蹒跚的老人。
街道上车水马龙,私家车、出租车、货运车,喇嘛鸣笛不断,一派热辣鲜活的场景。
在龙腾街边上的一家名字叫做中捷酒店的三楼房间内。
咔嚓咔嚓——
清脆的剪刀剪东西的摩擦声不时响起。
好一阵剪东西的声音停止了下来,又响起了哗啦啦的流水声。
杨楚鞠了一捧水洗了脸和头,站在狭窄洗手间间内,看着镜子中倒影出来的自己。
面容瘦削,颧骨高耸,微微凹陷的双眸,平静而淡漠。
一头杂乱的黄发已经被他剪成了寸头,额头上方有一道暗红色的伤疤,结痂不久,仿佛一条粗大的蜈蚣趴在上面。
全身上下有多处的伤痕,布满一道道淤青的胸前,一条条肋骨凸起,四肢干瘦,腹部凹陷了进去。
“这就是现在的我!”
杨楚端详着镜子里的面孔和身体,没有出现意识认知的错乱,这具孱弱、伤痕累累的身体,现在就是他自己。
在镜子前默默地站了一会,杨楚拉开了洗手间的门,来到了房间。
“……昨日跑马地马场上演谷草开锣战,骑师莫雷拉开锣日于尾场打后胜门后,将强势延续至快活谷。甫开赛已凭‘有苗头’先声夺人……”
床头墙角的一台黑白电视,正播放着昨日的赛马新闻。
杨楚在离开了青山公路后,花费了四百五十港币,就在龙腾路找了这家中捷的小酒店住下。
酒店房间只有七八平左右,大概是因为窗户小,又被其他的建筑物遮挡着着的缘故,尽管现在已经是上午十点,可房间内不开灯的话还是显得有些阴暗。而且因为建筑老旧,长久不通风,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种长期潮湿沉积下来的淡淡霉味。
从洗手间出来,杨楚走到了床边坐下,伸手将床头柜上的几个塑料袋中的一个,提到了面前。
先是将塑料袋里剩下半瓶的“黄道益”取出来,在身体几处淤青受伤的地方和骨头红肿的位置擦拭了一番,然后又拿出纱布在头上的伤口吸干净水珠,涂抹上膏药,最后再用纱布缠绕了两圈。
最后杨楚又在床头柜上的另外一个塑料袋里,拿出了三份盒饭。
两份叉烧,一份鹅腿,都是他让酒店服务员帮忙订的。
杨楚拿起一次性筷子,打开盒饭就往嘴里扒拉,他扒饭的速度很快,但每一个口咀嚼充分,吃饭的动作就像是一台在处理食物的机器。
一份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