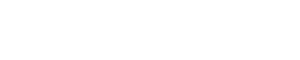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25节
作品:《新书精校版》人会走错。
这也是第五伦让人修的,无他,只因里民们方便太过开放狂野。很多人家没有厕溷,男人便跑到粪坑来解决,下裳一撩直接尿,甚至不顾路人目光一蹲很久,还有聊着天借厕筹的。
每次第五伦路过看到这一幕,都会眉头大皱,习惯了后世卫生文明的他,已经无法接受这光景了。
而那些贫民家的女子不好意思这样,便结伴去田间草中行方便,走老远憋坏了不说,若是不小心被人撞见或无赖儿偷窥,又是一出尴尬。
第五伦倒不是为了堆肥啥的,只是觉得……
这是中国,不是印度啊,焉能如此!
于是第五伦便让人修了这两间屋子,男女两厕间立了墙,男厕三个蹲坑,女则有五个。
在他看来,这本是寻常小事,景丹却露出了奇怪的神情,将第一柳打发到一旁,只招来第五伦,神情严肃,声音压低:“第五伦,我问你,你是如何知晓还未实施的朝廷诏令?”
啥诏令?第五伦一脸懵逼。
景丹道:“近来有人从常安回来,与你说过什么朝中机密?”
第五伦否认:“前些时日倒是有做商贾的亲戚来访,但吾等岂敢妄议朝政?”
见第五伦作此神情,不似有假,景丹更诧异了,其实此事再过三两日便世人皆知,说出来也无伤大雅。
他思索后道:“陛下昨日刚刚发来诏令,说孔子初仕,为中都宰,制为养生送死之节,长幼异食,强弱异任,男女别途,路无拾遗,器不雕伪,而今欲效仿孔子之政推行教化。这其中一项,便是男女别途!”
“可不止是路上要男女分道,陛下出巡见常安路厕男女混杂不分,易生乱淫有污道德之事,便下诏令,要常安及天下郡城中的路厕,统统改成男女分开!厕中要有隔墙。”
这事,负责掌管教化,又是郡大尹亲信的文学掾景丹自然知道,只是王莽没要求厕所墙上写字画图罢了。
皇帝王莽的圣人之意,与第五伦在里中所为,竟是不谋而合?
景丹还是不信,最后一次问他:“第五伦,你实话实说,究竟是从何处得知了消息?你说出来就好,我绝不会泄密,更不会追究。”
“文学掾,我确实不知,这第五里的男女厕溷,是十天前便修了的,里人可以作证,想来那时候,诏令还没下达罢……”
第五伦一边解释,心中却大呼卧槽。
“巧合,王莽不可能是穿越者前辈,这一定是巧合!”
而另一头,见景丹拉着第五伦单独说话,第一柳有些无聊地在旁边踱步,忽然看到地上有一摊水印和陶器碎片,似是有人匆匆行走不慎摔了没清理干净的。
他走过去嗅了嗅,眼睛顿时瞪大,又伸手沾了点尝了尝,顿时有了大发现。
就像抓住了第五氏的滔天大罪一样一样,第一柳全然忘了第四咸的劝诫,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,当着景丹的面,质问第五伦。
“第五孺子,我闻到了一股酒味,地上还有酒水痕迹,汝家莫非公然违反禁令,带着里民聚众群饮?”
就在此时,远处却传来一声哈哈大笑,却是带着族人迎过来的第五霸:“乡啬夫,你弄错了,吾等吃的不是酒。”
“而是醴(lǐ)!”
第16章 死狗
“吾等喝的是醴,少蘖(niè)多米,两宿而成,可甜了,乡啬夫、郡吏,是否要尝尝?”
第五霸说着,便让人端着一盆醴过来,确实有酒精的味道,但入鼻更多是粮食轻微发酵后的酸甜。大致可以理解成后世的醪糟、甜白酒,只不过原料是粟、黍,看上去颜色偏黄。
那么问题来了,甜白酒是酒么?
古人最重名实,不同东西必须取不同的名字,书经上说:“若作酒醴,尔惟曲蘖”。醴与酒一直是并列关系,一来用于发酵的不是朝廷严格管控的酒曲,而是麦蘖,也就是麦芽,根本无法控制。加上醴的酒精度很低,吃一整坛都不会醉,只会齁到。
新朝效仿周公《酒诰》禁止群饮,主要是为了节省粮食,而醴里醪糟比液体还多,用麦秆吸完汁水,剩下的当食物吃都没问题,不算太浪费。
所以若被人指责群饮,确实可以偷梁换柱后,扭头高呼:“你们要抓的是喝酒之人,与我吃醴的有什么关系?”
“我尝过了,就是醇酒!绝不是醴!”
第一柳却轴了,偏执地指着地上那滩水印和碎陶器当做证据,再次蘸了点放进嘴里舔了下,只差说一句:“文学掾不信也来试试!”
这确实是里民匆忙之中不小心打碎的酒坛,没来得及收拾,第五格等人有些紧张。然而第五霸却一言不发,径直走过去,朝旁边那条还在舔舐地上血迹污秽的狗子,就是狠狠一jio!
“死狗!”
那无辜的土狗今天挨了第二脚,一脸懵逼,汪汪叫着跑开了。
第五霸还捡起个石头猛地一扔,指着它破口大骂:“有人脚滑,不慎打碎了装肉汤的罐子,你这死狗吃矢没吃饱,竟跑来舔了半天,还撒了一地的狗尿!丢人!”
这是指狗骂柳啊!
第一柳脸都青了,末了第五霸还转过头,对他露出了笑:“不过,也亏得乡啬夫能从狗尿里面,尝出酒味来,不俗!”
第五伦别开脸忍住笑,你跟老爷子比阴阳怪气?
第一柳他急了:“你!文学掾,这老叟辱骂朝廷官吏。”
第五霸却摆手道:“乡啬夫,这罪名可承受不起,我虽是乡下人爱说粗鄙之言,但啐的明明是狗,何时骂你了?”
“第五霸,若没饮酒,你脸怎么红了?”
“太阳晒的啊!”
第五霸又能打又能说,第一柳嘴笨,浑身发抖,想向景丹求助。他以为自己这是身为啬夫举咎察奸,职责所在,不是兄弟争讼,加上证据确凿,上吏应该支持才对。
岂料一向待人谦逊有礼的景丹,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第一柳,眼中已生出几分不耐来。
难怪每年上计,临渠乡常是全县垫底,原来是摊上这么一位不识大体的啬夫。
我奉郡尹之命专程跑到这穷乡僻里一趟,是为了抓人秋社群饮?你见过哪家打鸣的公鸡跑去捉耗子。
“乡啬夫。”
景丹举手阻止了第一柳,不让他再难堪下去:“先前我不知今日乃临渠乡诸第秋社之日,故唤了你同行带路。”
“既然已经到了第五里,也找到了我要找的人……”
景丹看了始终缄默不言,只让祖父全力输出第五伦一眼,笑道:“那此处便没你什么事了,第一啬夫,还是快回汝家中,主持秋社祭祀去罢!”
……
第一柳遇上了社会性死亡的瞬间,面如死灰地回去了。
而少顷后,在第五氏坞院中堂上,就只剩下第五伦与景丹二人。
“文学掾,伦有罪。”
“何罪?”
“吾等秋社时喝的,确实是酒。”
方才的事明明都过去了,第五伦却不知哪根筋搭错,主动承认了秋社聚饮之事,他抢先告罪后,抬头看着景丹道:“想必文学掾也早已察觉了。”
景丹笑而不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