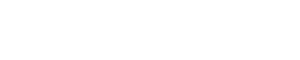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14节
作品:《汉阙精校版》地,对着巍峨汉阙稽首再三,痛哭流涕,举国为之震惊!
还有四年前,始元六年春(公元前81年),长安城除了召开盐铁会议外,还出了一个大新闻:汉武帝时出使匈奴,被胡人扣留多年的苏武,终于复归汉庭!
任弘听关中来客说,当苏武回到长安北阙时,哪怕是再熟悉的故人,也认不出他的样貌:
去时发髻乌黑的壮年使节,归来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,在人迹罕至的北海,渴饮雪,饥吞毡的日子太苦了,熬白了少年头,却磨不尽忠臣心。
和去时一样,苏武枯槁的手中,仍紧紧握着孝武皇帝授予的汉节,不论是起卧还是牧羊,哪怕节旄尽落,也不曾有失……
看着那光秃秃的节杖,从大将军霍光到长安普通里闾百姓,皆为之动容。
这一类的事迹听多了,哪怕是边鄙子民,大字不识,更不懂礼仪尊卑,但只要看到汉节,也会站直了身子,不敢丝毫怠慢!
这一幕,像极了两千年后的中国人,不管男女老幼,见到了鲜艳的国旗,不论何时何地,都得肃然起敬!
任弘也默默地站到徐奉德身边,感受着这似曾相识的场景,暗道:
“这就是两千年后,我们依然自称汉人的缘故吧……”
那八尺汉节,三重牦尾,承载了某种能跨越朝代的精神正气!
悬泉置众人就这样敛着手,如同行注目礼般,看着那汉节,以及持节使者的轺车渐行渐近。
轺车是汉朝官方车驾的标准式样,比战车、方厢车更轻便,车舆上方还有一个伞盖。
和后世一样,车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,比如驾车马匹的数量,就好比汽车的排量,八缸还是四缸,区别明显。
而车的构件质地,车盖大小用料,车舆的颜色,也是区分高低贵贱的好办法。
却见那辆驷马轺车顶上的车盖是皂色,两侧的用来挡泥的车轓(fān)涂成朱红色。
汉初时,因为是一群泥腿子大老粗打下的江山,礼制十分疏陋,直到汉景帝时,才完善了汉家的车马舆服制度。规定中二千石、二千石的车驾皆朱两轓,千石、六百石则只将左轓涂成红色。
虽然傅介子才是六百石的骏马监,但因为身负朝廷节杖使命,故车马形制与二千石同。
除了轺车外,随行人员也有不同规格,车前举着旗子开路的“伍佰”二人,左右骑吏两人,后面还跟着几辆副车,虽比不上郡守行春的规模,但也比县令出门排场大。
直到轺车在悬泉置正门前停下,任弘这才看清了傅介子的模样。
这位让任弘苦等多时的汉使年过四旬,身材壮大,赤面短须,那须显然是他自己修过的,显得十分干练。头上戴着一顶鹖冠,彰显英武,尽管连夜赶路,一对虎目中却看不到疲倦。
他身穿赤色丝袍,黑色下裳,腹部微微挺起,一柄长剑挂在腰带上,左手按剑,右手持节,哪怕下车时,汉节也没有丝毫放松。
徐奉德带着悬泉置众人行礼,不止是拜见上吏,也拜旌节:
“悬泉置诸吏卒,见过傅公!”
傅介子这趟出使经过的置所驿站,没有一百也有八十,这一幕早已司空见惯,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:
“吃食和茭草可备好了?”
徐奉德笑道:“都已备好,就等傅公到来。”
傅介子颔首,往前走了两步后,似乎想起什么,扫视在道旁迎接的悬泉置诸吏,问道:
“谁是任弘?”
……
悬泉置诸吏齐刷刷看向站在徐奉德身边的皂衣小吏,任弘遂出列,朝傅介子拱手:
“下吏便是任弘。”
方才,任弘看到傅介子的第一想法,竟不是等待多时的如释重负,也不是激动莫名。
而是琢磨道:“这傅介子果然身材壮大,比我还高一点,难怪一顿饭能吃两只鸡!”
傅介子不知任弘想法,上下打量他,问道:
“大丈夫无它志略,犹当效张骞、傅介子立功异域,安能久事笔砚间乎……这句话是你说的?”
“是下吏听闻傅公事迹,一时妄言。”任弘注意到,先前奉敦煌中部都尉之命,去迎接傅介子的苏延年、陈彭祖二人也在傅介子身边,定是他们说到自己了。
傅介子抚着短须:“志气倒是不错,但你觉得,我能和博望侯相提并论?”
任弘垂首:“博望侯使月氏、大宛、乌孙,凿空西域,西北国始通于汉。而如今西域已绝十余载,傅公复通之,此谓二度凿空。”
任弘真是佩服自己,二度凿空这种话也能想出来。
“傅公还在龟兹斩匈奴使者,壮我天汉国威,这件事,哪怕是博望侯,也不曾做过。想来傅公日后功名,当不亚于博望。”
“能说会道。”
傅介子看向同行的几位副使、官属,指着任弘笑道:
“汝等也能如任弘这般嘴甜,多夸夸我便好了。”
副使、官属皆大笑,徐奉德这时候却道:“傅公若是喜欢这小吏,下次再去西域,便带上他好了!”
任弘是万万没想到,徐奉德会这时候提出来,虽然听上去是玩笑,但副使、从吏的笑声却停止了。
那个站在傅介子身边,头戴长冠,留着长长胡须的副使摇头道:
“老啬夫说笑了,傅公奉朝廷钦命出使,每个随员都得上报朝廷,岂能任意加塞人手?”
徐奉德赔礼:“老朽戏言,戏言。”
他已经帮着任弘,试探了一轮,这件事果然没那么容易,不过,关键还在傅介子。
傅介子却不置可否,只是指着身后众多车马随员道:
“任弘,听苏延年说,你为吏十分干练,我这些属下吏士,你可得好好招待妥当了!”
言罢,竟径自向前走去。
“诺!”
任弘应了下来,却有些搞不清傅介子什么意思,还是徐奉德靠过来低声提点了他一句:
“这位骏马监,开始考较你了!”
……
“我想这傅介子,欣赏的是有条不紊之辈,可不会喜欢一个顾此失彼的人。”
徐奉德低声对任弘道:“傅公这次不是从大宛国带回了天马么,汗血马若是伤了病了死了,我悬泉置可担待不起。你且先在外安排妥当,再进去拜见不迟。”
他拍了拍任弘的肩:“勿要想太多,先做好本分事,我与老夏,在里面为你暖场!”
“多谢啬夫!”
任弘了然,便立刻引导使节团的车马,往马厩方向走去。
悬泉置厩屋顶上没瓦,只架橼木,上面铺一层密集的芦苇,然而再铺一层泥,反复几次,便足以应付敦煌干旱少雨的天气。
任弘早在上午,就已经来马厩巡视过了,厩啬夫和厩佐都是勤勉任职的本分人,早已为天马准备了两个最宽大的马栏,打扫得干干净净,还备足了供牛马食用的“茭”(jiāo)。
茭是牛马草料的统称,有麦秆、粟杆,也有牧草。悬泉置每天要接待许多车马,需要大量茭草,或来自于官府每年从田里收上来的刍稿,或是征募百姓在野外收割后交上来。
但驿马光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