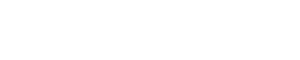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2节
作品:《汉阙精校版》有西域三十六国,各自言语都与中原不同,一般人去了,便是张口结舌,连顿吃食都要不到!你怎么办?”
任弘却笑道:“其实,我会说一点西域胡语。”
这下轮到陈彭祖吃惊了:“那么拗口的胡语,非得是典属国的译者才会,你竟也会?”
任弘解释道:“夏天时,有位西域胡商因故在悬泉置滞留两月,我便请他教会我楼兰话,虽不甚精通,但与之日常往来,足够用了……”
这半年光阴,他可没有虚度。
陈彭祖其实也只对西域道听途说,眼看没能难倒任弘,一时有些尴尬,只好向苏延年求助:
“苏兄,你当年去过轮台屯戍,你来说说看!”
“要我说……”
苏延年喝了口酒,补充道:“其实眼下西域最麻烦的,还不是风沙,也不是三十六国。”
他将酒盏重重一放,咬牙道:
“而是匈奴!”
……
“自从孝武皇帝罢轮台屯田,已过去十一年了!”
汉武帝时,汉军经常在西域用兵,自敦煌西至罗布泊,往往起亭,而轮台、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。
苏延年便是曾在轮台屯过田的老兵,说起这段往事来,感慨良多。
任弘知道,汉武帝晚年,关东民怨沸腾,但老皇帝就是我行我素,一心想着在有生之年,灭亡匈奴。
匈奴作为百蛮大国,东西万里,不是一两场战争就能消灭的,更何况汉武帝用错了将,对匈奴的战争屡战屡败,丧师十数万,差点将卫、霍早年的胜利全输回去。
战争不顺,汉武帝的性情也越来越暴戾,总怀疑有人要下蛊诅咒他,一连杀了三个丞相,两个亲女儿也下狱处死,天下人人自危。
直到酿成巫蛊之祸后,这位汉武大帝才清醒了点,在其晚年下了轮台诏,与民休憩,暂停域外扩张……
本来已要沸腾的大鼎,总算冷却了些。
但汉朝从穷兵黩武走向另一个极端,汉朝在西域的驻军田卒统统撤回,放弃经营西域,给了匈奴人重返那里的机会。
“这十一年来,汉兵再也没有西出玉门。”
身为军人,苏延年对此愤愤不平:
“反倒是匈奴人,驰骋于西域。吾等时常去玉门关,听那的候官说,从楼兰到大宛,单于使者威风无比,每至一国,城邦君王无不卑躬屈膝,他们甚至还指使诸国劫杀汉使,让大汉蒙羞!”
“就我所知,三年内,就有三起!”
陈彭祖接过话,形容起遭西域城邦截杀汉使的频繁来。
“若非如此,傅公在楼兰怒斥其王,在龟兹斩杀匈奴使节一事,也不会如此提气,眼下从玉门到敦煌,都在传颂傅公此举!”
“持节的使者尚且如此多难,更何况普通的行人商贾?更不安全。”
言罢,陈彭祖瞪着任弘道:“孺子,这下你还敢说去异域取功名的话么?”
任弘这次没有反驳,他默默起身,将两份符节交给苏、陈二人。
“两位上吏的传符,已登记完毕。”
“咦,你方才不是一直与吾等闲聊么?手头的活竟未拉下。”
陈彭祖踱步到案几前一看,却见胡杨木削的简上,的确已将他们的传符誊抄完毕,且那隶书字迹漂亮,这一心两用的功夫倒是少见。
任弘道:“我虽喜欢和过往商贾旅人谈话,正事却不会耽搁。”
他不再管陈彭祖出言讥讽,起身收拾笔砚,却听苏延年用拳头敲打案几,恨恨道:
“唉,若是长平侯、冠军侯尚在,岂能叫胡虏猖狂!”
长平侯是卫青,冠军侯则是霍去病,汉武帝时代响当当的名将,都已逝去多年。
任弘已行至门口,闻言后回头道:
“我窃以为,卫、霍虽没,但汉家儿郎的开拓凿空之举,却绝不会就此停下,每一代人,都会有新的卫、霍、张骞出现!”
“二君且待之,小子胆敢妄言,离汉军重返西域,驱逐匈奴的那一天,不远了!”
苏、陈二人有些惊讶,但还来不及细细品味这两句话,任弘却道:“对了,悬泉置的饭菜是敦煌九座置所里最好的,苏君、张君不妨吃了再走。”
言罢告辞而出。
陈彭祖反应过来,自己还是没有吓到任弘,遂追到门边大喊:“汉军很快就要重回西域?若真如你所言,我白送你一匹好马!”
但任弘却没有再回来。
至于苏延年,仍坐在案前,反复念叨着任弘的话,他已记住了这个悬泉小吏……
他的豪言壮语,以及大汉很快就会重返西域的预言。
苏延年暗道:“等吾等到了玉门关,再见到傅公,可得告诉他今日之事!”
二人不知道的是,任弘才走出传舍,便露出了得计的笑:
“有些话,由自己当面说出来好些。”
“但有些话,通过别人之口转告,效果更佳!”
第2章 丝路
“只望那苏延年、陈彭祖能帮帮忙,将今日一席话,传到傅介子耳中,不然就得等傅介子到悬泉置时,故意让置啬夫或夏翁提一嘴了。”
任弘心里如此盘算,他正是听闻苏、陈二人要去玉门关迎接傅介子,才故意投笔出言的。
不过,虽然陈彭祖有意吓唬,但所言非虚,西域确实是中原人谈之色变的凶险之地。
可风险越大,机遇也越大!
不,对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说,若想青云直上,这简直是唯一的机会!
这就不得不说说这“任弘”的身世了。
任家祖上也是阔过的,汉武帝时,任弘的祖父是朝中大员,曾做到过比二千石的高官。
只可惜任氏被那场著名的运动“巫蛊之祸”牵连,任弘的祖父被处死。幸好没诛三族,任氏一家被远徙敦煌,建设祖国边疆。
任弘那时候才三四岁,由父母带着,在寒冬腊月里往大西北走,遭逢大祸,宗族仆役尽散,唯独一个名叫“夏丁卯”的庖厨没有离开,车前马后,照看落难的主人。
中原人初至河西,水土不服,任弘的父母才到半路,便双双去世,只有夏丁卯尽忠职守,将任弘带到敦煌,主仆相依为命……
十多年过去了,不断有移民抵达,朝廷在疏勒河边设置了效谷县,夏丁卯被招到悬泉置的厨房里做事。而任弘也长大了,夏丁卯倾尽财帛,供他去县里拜儒者为师。
不过在记忆里,效谷县的那位郑先生,肚子里没多少墨水,既不通诗,也不会春秋,这任弘学了两年,也就学会司马相如写的识字课本《凡将篇》,摇头晃脑背一背“白敛白芷菖蒲,芒消莞椒茱萸”,字能认全而已。
好在任弘身强体壮,还会些角抵手搏耍剑的功夫,放在普遍文盲的时代,也能吹一句“能文能武”。
但祸不单行,元凤三年春,任弘从县城回到家,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风沙,在沙暴中晕厥过去,许久才被人救回悬泉置,求医拜巫,终于醒来。
不过醒来的任弘,已是焕然一新……
任弘自然不甘心一辈子呆在悬泉置,也曾试图有所表现。
上个月,敦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