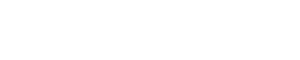第12节
作品:《庶子风流精校版》 嘉靖二十六年三甲进士熊勉学的《子曰:学而》,洋洋上千言,叶春秋看得一知半解,不过……这厮只是个三甲进士,out!下一个。
嘉靖二十六年二甲进士张居正。
这人倒是很出名,不过为什么是二甲,逼格太低,out!
这嘉靖二十六年的会试恰好考的就是这个题目,所以可以浏览的文章极多,最后叶春秋将目光定格在了该科状元李春芳的文章上。
文章好不好,尚且不论,可是状元公的文章拿来考一场童试,想必就是大炮打蚊子了,要低调?去他娘的低调,低调了这么久,叶春秋憋了一肚子的火,低调还考个屁的试。
打定了主意,叶春秋也就不迟疑了,顺着光脑中的文章直接下笔。
他的行书已经有了一些火候,平时练得多,今次不过是写千字的文章而已,一会儿功夫,文章便做成了。
来时,叶老叔公还教诲,说是文章先打一遍草稿,而后再正式抄录在答卷之中,可是叶春秋不必草稿,直接算是大功告成。
一抬头,天色开始亮了起来,进考场时是曙光才初露,乌漆墨黑的,而如今总算可以一览考场的全貌,叶春秋把考卷放在一旁用镇纸压着来风干墨迹,一面开始搜罗蒸饼和清水,饿了。
蒸饼硬邦邦的,只能就着一点清水吃。在叶家苦惯了,勉强也可以将就。
此时,所有的考生都在搔头摸耳,用心做题,这个考题虽然很大众,可是考的人这样多,若是不写出一点水平来,是很难脱颖而出的,因此不少考生反而很为难。
对面考棚的人不经意的抬头,见叶春秋刚刚消灭了小半块蒸饼,心里顿时一万个草泥马踏过:“这厮想必还没做题,居然还有如此闲情雅致,他是来考试还是来胡闹的?噢,对了,他是连子曰学而都背不出的叶春秋,连考题都不知所以然……想必就是来走过场啊……”
到了日上三竿,烈阳当空,对于考生们来说,这才是真正的考验,一面要搜肠刮肚的做题,一面是烈日炎炎,于是挥汗如雨,偏偏一旦汗水滴淌到了试纸上,又可能导致字体模糊,便疯狂的去擦拭额上的汗水,做完了题的叶春秋已经开始准备午餐了,午餐还是蒸饼,水深火热啊,叶春秋心里这样感叹,却浑然想不到同年们现在都还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一场考试下来,叶春秋是被梆子声吵醒的,吃了蒸饼就不免犯困,犯困了就要睡觉,一觉醒来,天要黑了,叶春秋不禁也佩服自己,忙是交了卷,出了考场,与叶家人会合。
叶老叔公的脸色不是很好,他这个年纪考试就是遭罪,几乎是被人搀着出来的。叶俊才几个一见到叶春秋,顿时围上来:“春秋,做题了吗?”
一般人出了考场,别人问的大抵都是考得如何,而叶俊才的话很伤人自尊,做题了吗?呃……我像交白卷的渣渣吗,巴巴的赶来考试,不做题像话吗?
倒是另一边,叶辰良出来,顿时许多人呼啦啦的涌上去,叶辰良面带微笑,颇为得意,道:“考得尚可,尚可。”
众人又问他破题,他脸上又添了几分神采,道:“学不轻仕,惟求其优而已。”
许多人沉默,这个破题很巧妙,从学而引申到了对学问的求索,一下子就把文章的逼格提高了几个档次。
有人道:“这是必中的了,莫说是童试,便是院试,也绝不会名落孙山。”
于是许多人感慨起来,自己怎么就不是叶辰良呢,瞧瞧人家,再看看自己,自惭形秽啊。
叶辰良看到了角落里的叶春秋,似乎忘了和叶春秋从前的嫌隙,一脸笑意地走过去,道;“春秋考得怎样?”
叶春秋晓得他今次考得好,所以得意洋洋,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拉出来和自己对比一番。
叶春秋笑道:“啊……我啊……我清早就做完了题,然后就吃了蒸饼,睡了觉,考得理应不错吧。”
县试是在卯时进行,那时候天还没亮呢,不过距离天亮也不过小半时辰,一般人做文章,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,叶辰良一听说叶春秋小半时辰就做完了题,居然还考得理应不错,就忍俊不禁,身边的人都笑了,叶辰良打趣道:“春秋有大伯任侠之风。”
任侠之风这句话,可不是说叶春秋的老爹讲义气,更像是任性胡为的潜台词。
叶春秋干脆盯着叶辰良的脸看。
叶辰良禁不住道:“你看我做什么?”
叶春秋笑了笑:“看大兄长得英俊而已。”
叶辰良摸摸脸,脸上的淤青还没消,跟猪头一样,他顿时恶狠狠的瞪了叶春秋一眼,心里骂着:“臭小子,等我中了童生,有你好瞧的。”
叶春秋懒得理会他,一行人回到客栈,过不了几天,县里就要放榜,不过叶家距离县城近,有专门的人在放榜之日去看榜,这么多叶家子弟留在县里也让家中的人挂念,所以在客栈里休息了一天,便打道回府。
第十三章 叶家出案首
“爹,我回来了。”
从县城回来,叶春秋的心情大好,县城终究不是自己家,而且天天看着叶辰良在自己面前晃悠,实在讨厌。还有叶俊才那厮,自从考砸了之后,总是一脸怨天尤人的样子,让叶春秋看着揪心。
叶景已从厢房里出来,一看到挎着行礼的叶春秋,脸上虽有掩饰不住的喜色,却还是假装板着面孔:“考得如何?”
“还不错。”
叶景一副我懂的样子,叹口气,知子莫若父啊,儿子说不错,绝不是谦虚,吹牛的嫌疑反而更大,于是他的眼睛眯起来,露出只有自己儿子才懂的高深莫测,摸摸叶春秋的头:“下次继续努力,路漫漫其修远兮,尔当上下求索。”
没办法沟通……
叶春秋心里摇头,我真的有这么弱吗?
……
而此时,在县城里,又是另一番的光景。
说到县试,其实只是科举最初级的考试,所以阅卷并不太正式,甚至童试根本不必糊名。
即便如此,本县的王县令对此却不敢懈怠,此时在后衙的廨舍,王县令坐在案牍之后,将教谕和书吏遴选出来的文章做最后的决断。
县令往往是进士出身,八股文的水平自是极为高明的,这使他应付这些试卷起来提不起兴致,童试的文章往往良莠不齐,有些文章水平低的可谓令人发指,从这么多的文章里,勉强有几篇还过得去,其中一个叫叶辰良的‘学不轻仕,惟求其优而已’的破题,也算是让人耳目一新,不过这在进士出身的王县令看来,也只能算是中上的水准罢了,勉强能应付院试,再往上就不太容易了。
宁波府虽处江浙之地,不过其民好从商,市侩气重了,文风不算鼎盛,所以王县令现在是矮个子里拔将军。
“今年看来大抵也只有如此了。”王县令的心里想着,最后几篇文章落在了案牍上,他随手拿起一份,单看这篇文章的行书,并不显得特别出色,可接着,王县令被吸引了,然后他眼前一亮,竟是爱不释手地抱着这份试卷,嘴唇轻动,不自觉的跟着文章轻声吟诵起来。
足足过了老半天,所有的文章大致已经批阅完毕,今年参与童试的考生有三百零九人,点选的童生五十余人之多,有书吏在王县令最后定夺了之后,便抱着所有的试卷前去封